
文艺评论丨潘凯雄看杨争光长篇小说新作《我的
策划:邵岭
如果作品不署名,只是看其文字,大概率不会将《我的岁月静好》与杨争光其名联系起来,不仅语言,包括结构、故事和他过往作品的差异都比较大。作品的故事倒是很简单,那个“我的”的“我”就是一个名叫德林者,作品主要说的就是他从青年到逼近中年的那段“岁月”。在他所在的那个县城,这“也是有影响力的人”,县档案馆至今还保留着他初二时的一篇作文。德林在县城一个中专任教时与自己的同事马莉也算是自由恋爱成婚,后来他考上了师大哲学系,继而又攻读了师大新传院纪录片专业的研究生而留在了省城。夫人马莉为了来到省城,也考上了研究生,一家人在省城过上了平平淡淡的日子。其实,就过日子而言,大多数国人何尝又不是如此呢?不过,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平淡的日子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没有波折:或许是因其过于平淡,倒是在这个家庭处于相对被动一方的妻子马莉率先有了外遇而提出离婚,而还在县城郊外的德林家老宅因其拆迁补偿的纷争又面临着被强拆的风险……
责任编辑:柳青
恕我直言,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坛,杨争光本是一个很难抹去的客观存在,虽称不上十分高产,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2年移居深圳之前,他较为集中地冒出的那些短篇《从沙坪镇到顶天峁》《蓝鱼儿》《高潮》,以及中篇《黑风景》《棺材铺》《赌徒》《老旦是一棵树》等,都是风格十分鲜明的独特存在。仅凭这些就足以奠定他在整个中国文坛而不仅止于陕西的独特位置,这些作品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依然并不逊色。长篇小说创作每一部之间间隔的时间虽长了点,但也有《越活越明白》《从两个蛋说起》到《少年张冲六章》这样三部可圈可点之作。谈不上多,但肯定也不能谓之低产。说句俗套的话,这样的产量特别是质量与杨争光现有的“知名度”与“江湖地位”显然不够匹配。
编辑:范昕
这样的逻辑自然是反常态反逻辑的。一个敏锐的作家不就是要抓住这个“反”字做文章吗?而且还要做足。我想,杨争光的《我的岁月静好》就是这种牢牢抓住反逻辑的典型。其实,当这种反逻辑行为一旦走向极端时,问题也就随之浮出了水面:这样的“静好”真的“好”吗?面对这样的问题,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概率都不会给出答案,而是让读者自己去认识、去直面、去思考,这,或许恰是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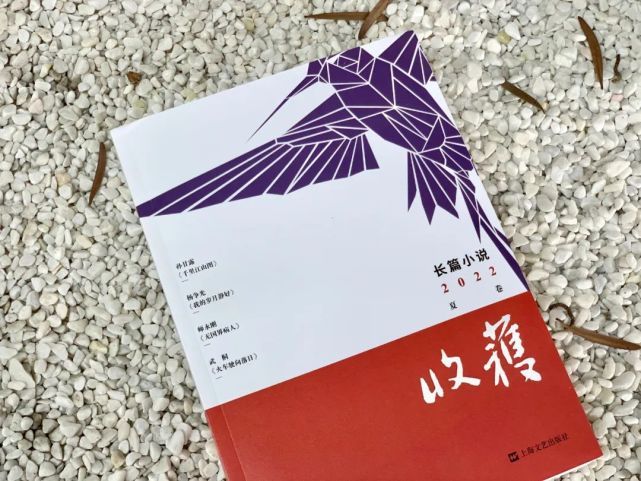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岁月”如此之“静”,真的“好”吗?
面对生活中的如此尴尬,依常理,置身于其中者即便是外在言行上可以尽力克制掩饰,面子上也可以做到波澜不惊,但内心不时泛起些许涟漪总是难免,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然而,杨争光笔下的德林与马莉,无论是行为还是内心的表现统统就是“静好”,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仿佛一切与他们无关。如此“静好”如果不是那种“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一时之忍,就只能是极端十足的麻木与麻痹,德林与马莉显然是后者,他们彼此实在没有隐忍的半点理由。
由十足的麻木与麻痹导致的这种“岁月静好”,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当下我们社会相当程度存在着的一种病态。目前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两种比较司空见惯的极端现象一是“喷子”不少、戾气太重;二是“躺平”者众、“静好们”多。在我看来,杨争光创作《我的岁月静好》其锋芒所指正是后者,他不仅用一种近乎荒诞的艺术手段平静地将这样的“静好”呈现于世人,也冷静地观察到“静好们”之所以能够“静好”,既有他们个体“与时俱变的创新”,更有“悠久的祖传”。“静好们”貌似冷静平静理性,究其实这不过只是一种假相,他们对社会之危害在某种意义比之于那些“喷子们”更恐怖、更具欺骗性。
就是这部小长篇新作《我的岁月静好》距他自己上一则作品《驴队来到奉先畤》面世的时间又过去了整整十年。当然,从这部新小长篇的“后记”中,我才得知杨争光在2012年竟突如其来地患上了抑郁症,那种既“没有纵身一跳”的勇气,又终日“生不如死”的感觉能撑出头已属不易,哪还顾得上写作的节奏。说句不太厚道的话,也正是因为杨争光能够从这场“劫难”中死里逃生的遭遇,才勾起了我阅读他这部新作《我的岁月静好》的强烈欲望。
作者:潘凯雄
据杨争光自述,“冀望岁月静好者似乎越来越多,自以为岁月静好的们在微信朋友圏的晒好也就格外显眼。”于是,这就刺激了他“想探究一下静好们的静好以及何以能够静好”?说实话,争光想“探究”的亦是我所好奇的,当然,我还有一层好奇就是想知道杨争光在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劫后会产生哪些变化?当然,真正的“岁月静好”也确是本人心向往之的一种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