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评论丨潘凯雄评鲁敏的最新长篇小说《金色
再往下排则要轮到有总的两位公子了。一位是自打出生后便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老儿子穆沧、活脱脱地“一个老傻子”;一位则是被有总寄予厚望最终却偏又成为“忤逆子”的次子王桑,在有总的精心设计悉心打点下,大学毕业的他顺利成为公务员队伍的一员,只是这位逆子在机关改革普查大家意愿时,竟然选择“服从安排”而最终被外放到一个名为“凹九空间”的所谓展馆。这个“惊天之变”不仅让有总“打死也想不通”,更令他烦心的还在于这位“忤逆子”竟然又是个“丁克”,如此这般穆家岂不要“绝后”?
经过以上概要的解析,可以小结一下我所认为的《金色河流》是“鲁敏作品中内涵最为复杂、表现力格外讲究的一部新作”的理由了。鲁敏过往的创作看似注重客体呈现,实则更在意的是主体探微,但两者转换间多少还是存有些许缝隙。这种缝隙其实不在大小,但凡露出一点便会令人有不爽之感,至少本人会这样。而这部《金色河流》的“内涵”尽管比鲁敏过往的创作要“复杂”得多,但因“表现力格外讲究”,过去那种多少要露出点的“缝隙”也随之消失。这其实很不容易,究其缘由,我想首先是有总这个人物被她“惦记了许多年”,“惦记”时间越长,对这个人物也就吃得越透,本是作为客体的表现对象不知不觉中已化为自己主体的一种倾诉,表现在创作上便是通过某种得体适宜的形式进行传输。具体到《金色河流》中,两种视角的使用也好,将叙述时长控制在有总生命的最后两年也罢,以及由此延伸开去的种种,其实都是为鲁敏感觉传输起来得体适宜的一些形式,而反过来,这种得体适宜的形式也因其对有总的“多年惦记”而产生了浓郁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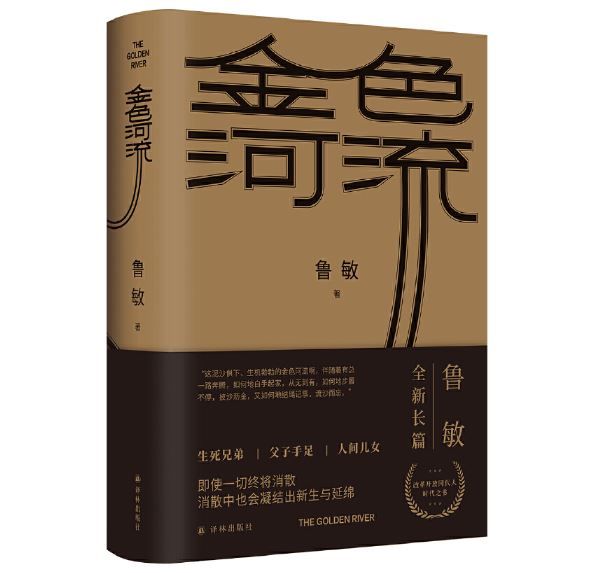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谢老师当是这条“河流”中的男二号,也是我所读过的文学作品中似乎还从未见识过的这样一种“人设”。曾经报道有总属下“童工瞎眼”深度新闻的“良心记者”竟摇身一变成为有总身边的公关总监,地位相当于有总那“小小王国的国师”。如此“卖身”的他当然有自己的小九九:为“复仇”而“卧底”。为此这位谢老师还“正儿八经地启用了专用笔记本”,分别将自己的记录与思考编号为“素材X”和“思路X”。“思路”虽在不断调整,但“素材”则累积下了一百多条。只是在这漫漫的“卧底”和隐忍中,这位本意欲为“复仇者”的谢老师竟不知从何时起悄然变成了有总的知己,而有总这沙里淘金的斑驳来路到底是一部“奋斗史”还是“罪恶书”也随之成为一个大大的问号。
有了人物角色上这种古怪精灵般的设置,接下来就该看鲁敏在《金色河流》中是如何组织叙事的了。作品用宋与楷两种字体分别排列,其中宋体部分是作家的全知视角,也是作品叙事的主体;而楷体部分则是有总个人的内心独白,或回首往事、或琢磨着自己的身后安排。两种视角构成某种互文性,虽以全知视角为主体,但将有总的部分内心活动与往事回首特别地以其主体视角呈现,除去使之突出外,更有一种逼真感。这种浮在面上的叙事设计似乎不难理解,而更有意味的则在于鲁敏在全知视角叙事时的那种编排与剪辑。
姑且先粗暴地无视一下鲁敏精心设置的这条“河流”之蜿蜒以及其中泛起的“金色”。一言以蔽之,《金色河流》以近40万字的篇幅无非是在讲述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穆有衡(有总)大开大阖的人生历程,包括与子女的相亲相杀、与兄弟的相依相弃。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个企业主的创业故事或一个家族的故事却被鲁敏给叙述得蜿蜒起伏、金光四溢,而导致“蜿蜒”产生“金光”四溢的主要元素大致如下。
先看这部长篇小说几位主要角色的设置。
鲁敏的小说创作虽还称不上特别高产,但肯定是一位有着足够体量与分量的作家。我对她作品的阅读虽谈不上系统,总体上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她的创作看似一种写实,但裹藏于“实”背后的主观性、精神性因素还是要更多一点。无论是早期对人性中浑浊下沉部分的敏感,还是接下来那些被称之为“东坝”系列的作品中多了些“温柔敦厚”的乡土情怀,直至再往后到长篇《奔月》中用十分生活化的大量细节来表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样一些人类哲学思考的终极命题……凡此种种,从鲁敏过往创作中缕出的这条线索我虽不敢言十分确切但也好像还不至于十分牵强。而到了鲁敏最新问世的长篇小说《金色河流》,姑且放下作家表现力的主客观比重这个话题不论,这都是我看过的鲁敏作品中内涵最为丰富、表现力格外讲究的一部新作。
